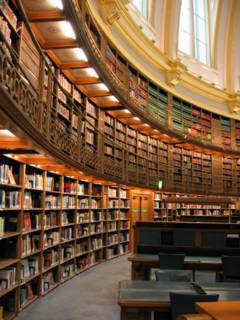這裡是Leicester Square附近的Pret A Manger。位於William IV Street和 St Martin's Lane的交界,正正對著我的是Charing Cross Road。往Cappuccino倒了三包糖,聽著爵士化了的聖誕音樂,看過地圖確認了位置和之後的去向後,心情才好起來。走得很累,又餓得很!現在終於舒服一點了。
* * *
這天的心情很反覆,不過基本上都處於負的狀態。
一早起來便發現時間不多,要趕快梳洗才來得及吃早餐和乘飛機。整晚都睡得不大好,就是因為害怕今早起不了床,每一兩小時便下意識醒一醒。(這幾晚做的夢怪怪的,有好多回憶,又有很多不祥的預兆。)幸好早餐不錯,荷蘭式的選擇讓我感到親切。從旅館走往火車站那段路,整個阿姆斯特丹都被霧籠罩著,像還沒睡醒一樣。阿姆斯特丹很不適合早上,太和善了,它根本從不善良。一開頭以為自己已懂得一點點語言,且在荷蘭住了一陣子,要掌握這個城市應該不難,誰知還是被冷落了。
坐在往阿姆斯特丹Schiphol機場的火車上,我不停說服自己:我在去倫敦。
* * *
Check-in那些也很順利。拿著護照和機票,感覺很成熟似的,說乘飛機就乘飛機。時間又掌握得不錯,心想這個旅程開始得真好。暗喜之際,把不寄艙的背包放上金屬探測器的輸送帶。〔先生,可否把那把刀拿出來看看?〕我隨即冒一冒汗,我的萬用刀。為什麼我一直都不信邪呢?一直都天真地一廂情願地覺得帶這東西上機不會有事... 雖然這刻也不明白當時的邏輯是什麼,完全不知道那時為什麼不把行李寄艙。總之,折騰了幾回,唉,終於被沒收了。〔我有沒有可能在回來時把它拿回?〕〔I'm sorry. You'll lose it.〕那個男的飛行服務員已經很有禮貌又很同情的樣子,只是真的於事無補,我整程飛機也為了一把萬用刀很沮喪。怎說那也是小時當童軍買的,伴了我好多年;即使未必在旅程中很有用,但帶著它安全感大多了。連唯一的依靠也沒了。Confiscated。完全消失。
* * *
在天上看到倫敦,心是開朗了一點。第一次離開荷蘭!過關後打算立即找個資料中心問問怎樣乘車到旅館。這次的確有點鹵莽,之前沒有查看從Luton機場到旅館的方法,甚至不知道Luton在倫敦的哪裡。在機場找了一會,找到的郤只有數部電腦:自己查!完全不會查。不想浪費時間,就直接走出機場看看有什麼可能性。很荒蕪似的地方。幸好讓我看到巴士車身上有London Bridge地鐵站的字樣,就到巴士的櫃檯問問。但我聽不清他叫我乘車到的地方的名字,什麼pancreas!完全適應不了他的口音... 反映的是我自己的口音才最奇異,又不美式又不英式。最後get到接駁巴士是免費的,我就不顧一切離開了機場再算。到達一個類似火車站的地方。救命,我發現自己是完全不了解英國的鐵路系統的,這個系統和常常看到的underground有什麼關係?我不怕問人,唉,只是他的口音又令我覺得自己是完全不懂英語的。再問有沒有什麼Railcard類的東西,他沒什好氣,只說什麼pancreas。我還是不要輕舉妄動,買張單程票再算。太可笑,連目的地是什麼都不知道,到了那裡要如何到London Bridge站又不知道。從沒試過這樣沒把握。隨手拿了張地圖又不甚懂看,只好到了pancreas再算!看到火車來,我才知道我的目的地其實叫St Pancras。
兩次的(不)溝通經驗,令我又覺得被遺棄。原來我來自荷蘭。除了〔用荷蘭語拼讀英文字母組合〕的習慣外,我還會多荷蘭呢?突然想起荷蘭人會問我〔how do *you* say it in English?〕。我?原來我的英文只是勉勉強強。來到這裡,以為多懂一點這裡的語言會容易點生活,可以仍要用另一套方式去適應... 我不屬於荷蘭,同樣不熟悉這邊的文化。
St Pancras賣票的先生還算好人,就信他買了一天的travel card。我裝著稔熟地不看地圖走到King's Cross地鐵站,以為這樣會安全一點不會被人看作easy victim(但其實我是背著極大個背包的)。忽然驚覺四個月來都沒有乘過〔地鐵〕!〔這就是城市的產物...〕我被自己的大鄉里想法嚇一跳。
* * *
街道和行人給我的印象都很熟悉,就是很像香港。本來解釋不了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;後來發現簡單如過馬路時望哪邊便是了:荷蘭的車子方向盤都在左邊,英國則和香港一樣在右邊,行車方向我原來一直已習慣了。雖然迎面走來的都是鬼佬面孔(噢英國人),交通燈,路牌,等過馬路的小機器,一切也和香港很像。我想家了。
* * *
先到遊客資料中心拿張地圖,知道自己原來很近泰晤士河的南岸,再問問人便走到河畔了。運河,大橋,全都極壯觀,極浪漫。運河是一個大城市中不可或缺的,就是那種氣派。我沿著河邊的路一直走向夢寐以求的Tate Modern。誰知先遇上莎士比亞的Globe Theatre!我完全不敢相信我的眼睛,我真的來到了。上個星期文學課的主題是喜劇,文本為〔仲夏夜之夢〕,當然還談到莎士比亞時代劇場的特色。對那劇場的印象只是一張畫,這刻我竟然到達現場來,當然趕快買票進場。聽著講員的介紹,我坐在那個倣製劇場的觀眾席上幻想當時的情景。現代劇場中觀眾可以很懶惰,坐著等人餵。反觀幾百年前的劇場,雖然原始,但人要很主動,幻想力很豐富才可真正欣賞到一套劇。森林,皇宮,天堂,全都放在這個空蕩的台上,就靠劇作家的語言和觀眾的腦袋呈現出來。這是一門更像閱讀的溝通,是劇場的另一個層次。而莎士比亞劇場的設計概念〔舞台就是世界〕也很震撼:舞台頂,台面和台下的空地構成天,地和地獄的概念;所有觀眾又圍著舞台坐或站,凝聚成一個微型的世界,就是一個Globe。從沒想過劇場本身已很有傳奇色彩。
很餓,但抬頭一看見Tate Modern的煙囪,二話不說進去才算,實在太型!呢D就叫做空間感丫唔該。從底層的Turbine Hall走進去,令我想起機場通道的寬闊和高度。兩旁有些怪聲一直傳出來,設計很幽默;後來才知道那是其中一個展品,Bruce Nauman的詩被不同人朗讀出來(這個simulation極像我當時走過那通道的感覺:
http://www.tate.org.uk/modern/exhibitions/nauman/)。我急不及待拿了地圖就往第一層走。好想盡快把所有東西看過,又要按著好奇心每個作品小心地看,又急又矛盾,像收到信拆開時的興奮。每層的展館都是連著的,第一次走進去時和走進迷宮一樣,一看地圖又發現那其實很簡約易明。所有作品對我都很有衝擊,視覺上的,觸覺上的(用的物料)。最喜歡是After Duchamp的展館,令我對Duchamp很有好感。只看了一層便快休館了,我一定會再來的。
* * *
非常餓。但也決定走過Millenium Bridge,再走到Leicester Square先熟悉一下明早買音樂劇門票的地方。從地鐵站一出來,這個地方比銅鑼灣還要擠!人人也很美,都穿得很體面。很有不屬於自己的感覺,已很久沒見過這樣的人多車多。今天走得太累了,終於撐不住便在Pret A Manger坐了下來吃點東西寫點字,到現在打烊了。決定往soho和唐人街那邊走去。
* * *
隨意走走是很有趣的。我沒看地圖,只管向著那個方向走。經過一個廣場,看到裡面有很多聖誕節的攤子和機動遊戲,晚上所有燈都亮了,人又很多,竟然想起〔鳳蕭聲動,玉壺光轉〕。走到一個商場,那是晚上九時半還開著的商場,根本不能在我的城市見到。有一個橫跨幾層的大型遊戲機中心,設計成一定要把幾層都走過才能找到出口離開。裡面我見到有很多中國人或是日本人,難道只有亞洲人才這麼無聊,走在一起都不懂溝通,唯有一起玩玩遊戲罷了。再進了HMV,噢,家的感覺!很久沒到過HMV!荷蘭的唱片店制度很白癡,客人要拿著放出來的空唱片盒到櫃台問職員拿唱片;但問題是那個被人亂丟過萬次破破爛爛的盒子就是你的了,而且他們有可能只有唱片而沒有盒子也收你一樣的價錢。我真的受夠了這樣低能的安排,完全漠視唱片盒子和裡面小冊子的重要性!我想這裡不會這樣吧。連忙看看唱片的價錢,沒有驚喜,還是太貴了;難怪外國人到香港的HMV是會攜著籃子掃貨的(只是他們知道旺角的話必更心痛)。排行榜上,依然是U2〔how to dismantle an atomic bomb〕第一,還有Robbie Williams,Kylie Minogue,Keane,Maroon5,Green Day,Natasha Bedingfield,新興的Al Vino也像很紅似的。我才突然意識到我真的來了英國!在荷蘭我每天也會聽BBC radio1,習慣了他們的音樂選擇,現在才醒覺自己和每天聽的東面那麼近。那些歌,那些人,救命,我原來在倫敦。
因為想省點錢,常常都在飢餓的狀態,即使走過唐人街也沒進去吃飯。再走過Reagent Street,感受到久違了的城市晚上氣氛,霓虹燈,車,人,食店。沿著Reagent Street和Oxford Street走總讓我想起彌敦道,只是兩旁的大廈不再是籠屋,店子沒有賣參茸海味或VCD,街上的人也漂亮得多。又有被淹沒的感覺,作為一個中國人在這裡真的沒什麼,有誰會看你一眼?總覺得在這裡住的中國人被他們看得有點低下。... 唏,我是遊客,(理論上)會花錢的人,別看不起我。(這是什麼心態?!)